全球视野下的二战叙事与中国抗战|《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来自中国的“新”声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持编写了《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并以中、英文两个版本出版面世,向中文世界与西方世界表达了新时代中国学者在二战研究领域的“新”声。所谓“新编”,何以为“新”?围绕这一核心问题,澎湃新闻采访了编纂团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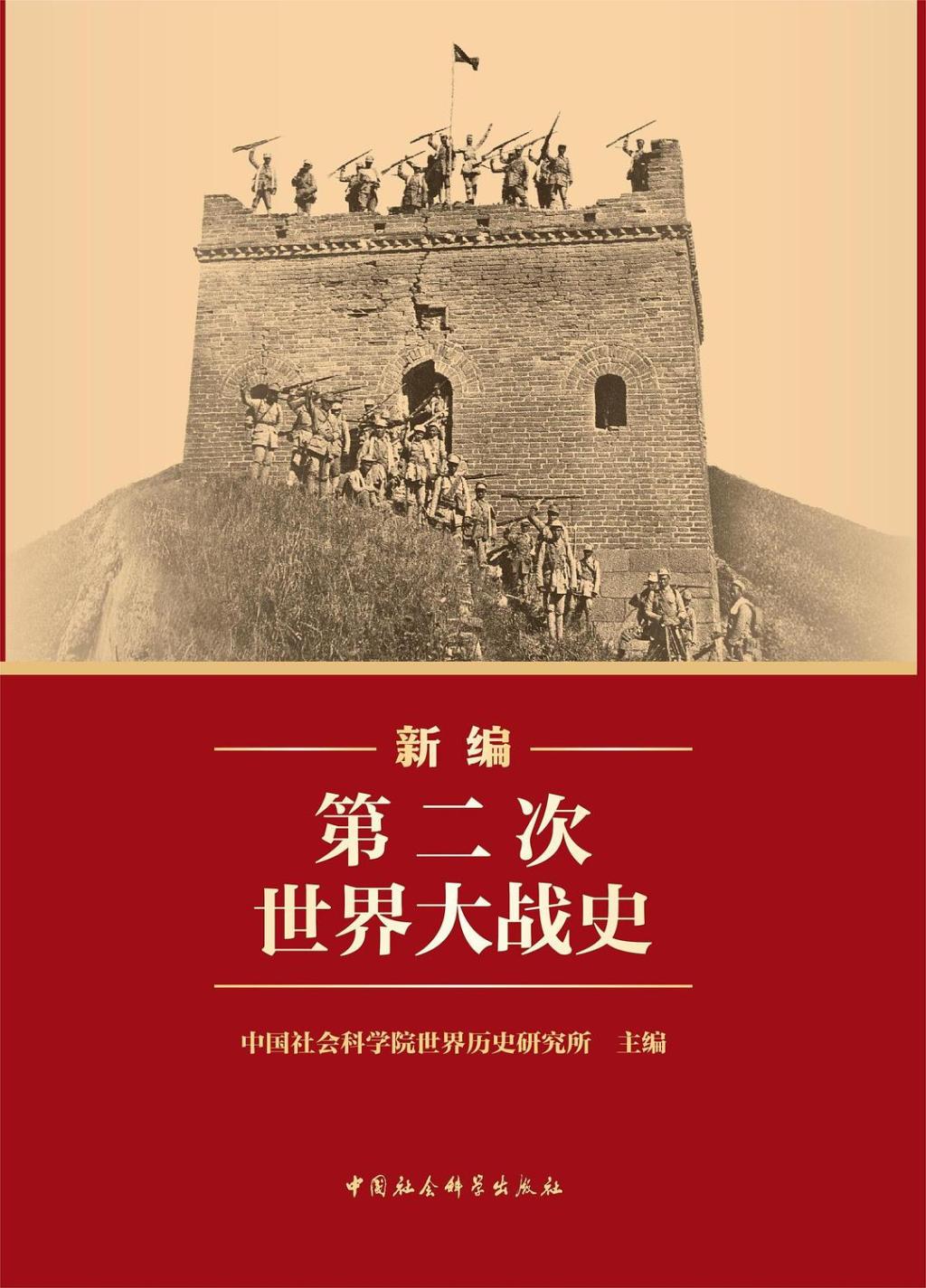
《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文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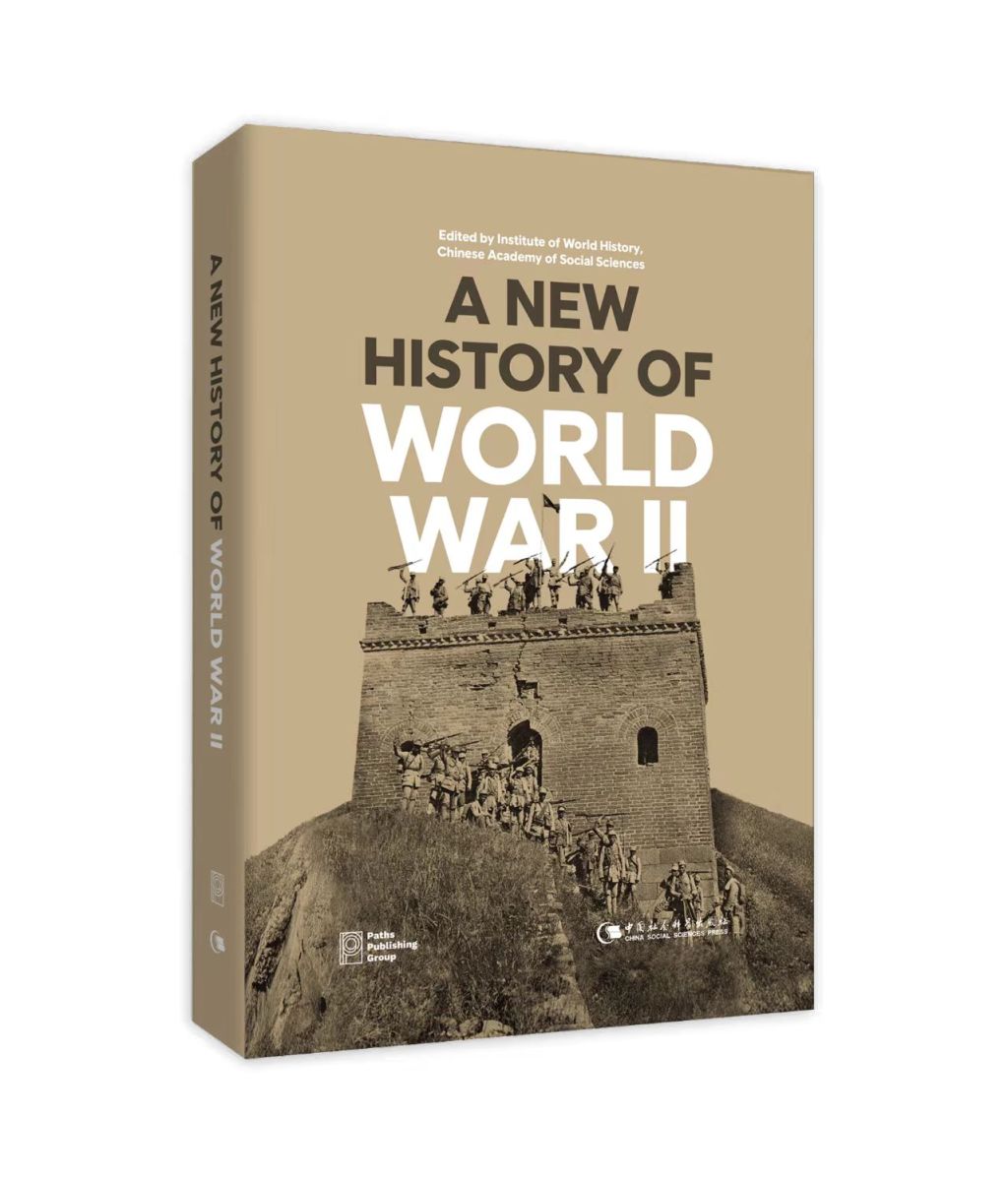
《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英文版
来自中国的二战“新”声
《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是凝聚国内二战史学界集体智慧的成果。本书顾问团队由国内世界史学界、二战史学界的数位资深专家组成,三十多位作者来自中国历史研究院、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十余家科研机构和高校,均是二战史研究领域的中青年骨干。
内容方面,既谓“新”声,自然就有与其相对的旧观点、旧叙事。这指长期以来,国际二战史研究领域存在的“西方中心论”——过分夸大西欧战场的作用,弱化甚至无视苏德战场、中国战场的历史贡献。接受采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王超华研究员即以一例说明。
“英国著名战略学家、二战史家利德尔·哈特曾在冷战期间(1970年)完成一部二战史,被西方学界奉为经典。在书中,作者用了大量篇幅讲述欧洲战场以及北非地中海战场,关于苏德战场的篇幅不多,关于中国战场的内容更是少得可怜。在讲述苏德战场时,作者又过分强调德军后勤困境等因素,而轻视苏军战略反攻的主动性。这种叙事模式至今仍在许多西方二战史著作中延续。它们往往否认东方主战场、苏德战场、抵抗运动的重要性和贡献,淡化甚至美化侵略战争,扭曲了历史真相,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历史修正主义乃至新法西斯主义史观滋生蔓延。”
为此,《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运用英、德、意、俄、日等多语种的史料研究和创新的理论框架、内容编排,对西方二战史叙事进行了系统性纠偏,以期客观呈现各参战国的历史贡献,重构符合历史真相的全球二战认知框架。王超华指出,相对于传统叙事,《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放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中进行考察,深入阐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以巨大民族牺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和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
(2)客观评价了苏联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贡献。作为二战欧洲主战场,苏联是抵抗德国纳粹主义的中坚力量。苏联红军的英勇作战,碾碎了纳粹侵略者的野心,解放了被德国法西斯奴役的人民,书写了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壮丽史诗。
(3)重点考察了反法西斯盟国的外交互动与战略协同。第十章讲述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建立的过程。第十三章则是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的相关内容。在战略协同方面,《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还讲述了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配合了盟军在东南亚的战略行动,美英盟军诺曼底登陆则与苏联成功实现了对德国的两面夹击。
(4)专辟一章(第九章)论述法西斯的“新秩序”迷梦及其在战争期间犯下的滔天罪行。德意日法西斯所实施的种族灭绝与大屠杀、活体实验与性暴力、财物掠夺和强制劳役等罪恶行径充分暴露了法西斯主义反人类、反文明的本性。
(5)全面加强对欧亚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运动,非洲、美洲和大洋洲人民对反法西斯斗争的支援,反法西斯盟国的战略协作和相互支持等问题的叙述,努力完整呈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全貌。
(6)详细论述了战后审判的过程及其历史意义。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把战犯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的正义性质、历史价值、时代意义不可撼动。
寻声:二战研究的全球史转向
《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凝聚了国内二战史学界的集体智慧,同样也反映了国际二战史研究的前沿趋势。
近十年,二战史学界出现了“全球史整合”趋势,在此趋势下,已有国际学者将中国抗战置于全球反法西斯框架中考察,方德万、拉纳·米特的研究即是其中之代表。
8月18日,现就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的拉纳・米特应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高端论坛第五讲”发表演讲,主题为“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抗日战争研究的新路径:对历史叙事与编纂的反思”。在这次演讲中,他指出,中国抗战在西方长期被边缘化,主要原因包括西方军队未直接参与中国战场作战、中日语史料存在研究壁垒,以及战后档案获取困难。但他同时表示,近年来英语学界对该领域的关注度已显著提升。
《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系统吸收了十余年来国内外学界取得的重要突破性成果。这在二战起始时间的界定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关于这一点,王超华研究员做了更为详细阐述:
传统学界通常将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作为二战爆发的起点。但随着中国战场受到更多关注和更为深入地研究,以及以全球史为代表的新的研究范式的出现,上述带有明显“西方中心论”色彩的观点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十多年前,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方德万就曾提出,中国抗战所经历的遭遇、创伤以及牺牲与其他战场相比有很大不同,因此应重新确定二战的分期,如果从亚太视角来看,二战的起点应该是1937年7月发生的卢沟桥事变。拉纳·米特也主张将卢沟桥事变作为二战起点,因为自那时起,东方战场便已开辟,对世界局势产生重大影响。也正是从这一天起,法西斯轴心国完全暴露了其欲占领世界的野心和阴谋。他还指出,中国是第一个面临轴心国侵略的国家,在很长时间里,独立抗敌,苦苦支撑,极大地消耗了日本国力。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种重要角色、巨大作用长久以来未得到西方学界关注和重视。
“1937年卢沟桥事变起点说”有进步意义。但日本侵华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是1931年9月18日。不少国内研究将九一八事变作为二战起点。例如,胡德坤、罗志刚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纲》(2005年)、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写的5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2015年)均有类似表述。2017年,“十四年抗战”之说被写入历史教科书。
而随着全球史的兴起,西方二战史书写产生了一批具有创建性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均将九一八事变作为二战起点。2019年,安德鲁•布坎南出版的《全球视野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认为,二战既是全球相互联结的一个站点,也是20世纪中叶混乱蔓延的一个事件,或者说是一系列相互交织的事件。它不是一场双方界限分明的单一战争,不能被强行纳入传统的1939—1945年的时间框架。它是在日本自1931年开始在中国和东南亚发动战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022年,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教授理查德•奥弗里出版的《二战新史:鲜血与废墟中的世界:1931-1945》也将二战的起点定在1931年。他认为,二战应该被理解为一场全球性事件,中欧、地中海地区和中东,以及东亚的区域不稳定都促成了更大范围的全球危机。从全球视野来看,九一八事变标志着,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深处,日本试图通过暴力建立新的帝国和经济秩序,标志着新的帝国时代的开端。亚洲战事及其结果对于塑造战后世界的重要性不亚于在欧洲击败德国,甚至意义更大。
从历史事实来看,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发动侵略世界战争的开端,中国人民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由此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理应是二战的起点。因此,《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在第三章中明确提出了这一观点。
除此之外,国内外学界关于战争记忆、战后国际秩序、绥靖政策、法西斯主义等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在新书中亦有体现。
时代之“音”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秩序面临深刻调整的今天,中国学者集体编撰这样一部“二战史”著作,无疑更具时代意义。对此,王超华研究员也表达了他的看法。
“错误的二战史观导致人们对二战的认知产生了许多偏差。最为严重的是某些势力对侵略历史的美化与否认,不仅严重伤害受害国人民的感情,更威胁到战后国际秩序与和平理念。”因此,《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那段历史,把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以事实批驳歪曲历史、否认和美化侵略战争的错误言论。
“在内容安排上,我们的新书没有停留在1945年战争结束,而是延续到战后,客观还原战后国际秩序形成的过程以及中国在其中的建设者角色。”《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从战后政治、经济领域全面探讨了中国大国地位的确定。中国在战后国际秩序中的重要地位的获得,并非来自别人的赐予,而是中国人民用英勇战斗和无畏牺牲换来的。
“此外,我们想告诉世界的是,中华民族热爱和平,我们开展二战史研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唤起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珍爱和平、维护和平,让世界各国人民永享和平安宁。所以,当前的二战史研究成果不仅应是过去的回响,更应是未来的镜鉴,是培育和平理念的精神教科书,应厚植人文情怀,更多关注战争阴霾下生命的韧性与人性的光辉,努力唤醒人类命运与共的集体意识。”
《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以一定篇幅讲述了中苏、中美互帮互助的故事,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人民支援反法西斯斗争的故事,中国人在中国之外参加反法西斯斗争的故事,白求恩、柯棣华等反法西斯主义战士投身中国抗战的故事,拉贝、辛德贝格、魏特林等千方百计保护中国人的故事,何凤山拯救犹太人的故事,中国军民奋不顾身救助完成“杜立特空袭”后在中国弃机跳伞的美国飞行员的故事,等等。王超华研究员表示,讲述这些故事的目的在于,通过这些真实、客观、全面又充满人文温度的历史叙事,宣示中国人民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积极姿态,同时呼吁国际社会推动和平的信念代代相传,为世界稳定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